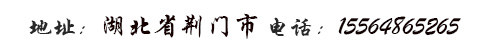散文飞幡青烟化永思文化快讯
| 在我故里石牌,安息着几位亲人,几年没回去了,今年清明,我去给他们上了坟。曾祖传到我父辈,存下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(改为慧)”四男一女,到我记事时就只见到了父亲和四爸(讳“克智”)、二爸(讳克仁”),“礼”“慧”已殇,一个殒命日本飞机弹下,一个死于癌症折磨中。三位前辈都活到将及九十岁先后仙逝,其中,四爸二爸就安葬在石牌。上世纪那段混乱的年代,“破四旧”破除了千百年来“死人为大”“入土为安”的传统观念,从前修祠堂、建墓园祭祀祖先的礼仪,被“扫除封建迷信”的铁帚无情扫荡一空,大约从七八十年代起,石牌人老了(去世),只得找一处野冈荒坡落寝。不知是什么人先找到了烂泥湖边的这块荒坡,大约是湖水逐年退缩,渐渐让出的地脚,远望低于周边田畴,走近大小还算是个小冈,于是石牌街上老去的人就前前后后、不请自来到这里聚息,荒坡自然而然成了石牌的一块坟场。到我四爸二爸去世时,这片坟场地势高的地方已无插针之地,只能葬在边缘。四爸去世次年,我来给他上过坟,记得四爸的坟就在进坟场的路口,二爸的坟则要穿过坟场,到那边的边缘。清明前又下了几天雨,直到当天上午还“淫雨霏霏”。下午,我来到堂弟昌能家,约他领我去上坟。昌能上午已与自家兄弟姊妹们上完坟,按习俗不能再来故人坟前,他把我送到坟场旁的路边,上坟我一人下车自去。这里真是名不虚传的烂泥湖。退化成坡的冈地内硬外泥,连日阴雨雨水只浸润了浅浅的表皮,底下硬硬的生土,雨水过后冲下坡去,地面就是稀泥。有坑洼不平的地方,就留下一汪汪水,来上坟的人脚踩稀泥,在倾斜的地面滑出一道道划痕,低洼处踏水而行,积下的雨水立马成一方浑浊甚至是一团泥浆。我穿着昌能预先准备的长统雨靴,小心翼翼地滑到四爸坟前,靴变成了泥靴,裤腿上仍粘了几处污泥。四爸坟茔上草青了枯、枯了青已将及十轮春秋,如今满封的草又重现青葱,青葱的坟头上插满鲜艳的清明吊子,那是先来上坟的昌能兄弟姊妹们留下的祭奠,他们有的从广东东莞回来,有的是从宜昌、荆门、钟祥赶来,差不多年年如此。清明吊子是招魂幡,招徕逝去的魂灵来接收后人的祭供。坟前的墓碑素颜纯青,清晰地镌刻着四爸四妈的名讳、生辰忌日,一连串立碑后人的落款,清楚记录着不可磨灭的亲缘血脉,荐于世,示于人,贡于天。这是人间最真实最牢固的存档,最亲近最坚实的链接,也是最强劲有力的磁石。正是它的链接和吸引,使得阴阳两隔的人亲亲相连,铸就出中华民族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千古丰碑,千百年来,凡是炎黄子孙,都记着它,想着它。无论是达官贵胄还是凡夫俗子,每当清明节来临,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哪怕千里万里、哪怕刮风下雨,都要来到这块碑前。一周前,我就从沙市奔到钟祥来到了父母的墓碑前。父母安息在钟祥城东一处木秀林幽的山坡上,下了车还要走几里路。因为疫情阻隔,去年误了清明上坟,两年未修葺整理,坟周围满了杂草,窜生了一根根一方方新的刺芥、荆棘。坟茔上长满藤蔓青蒿,更有好些粗过几指的刺枝从几米外蓬过来,遮住半边天,使得四周更阴郁幽寂。那天我事先借了砍刀,砍枝斩刺,除草清场,两小时下来,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汗得透湿,双手都带了伤痕,再看父母坟上,露出了明朗的天空,驱除了先前的幽暗,那边茂林深处,传来声声“布谷”,打破四周的静寂。整理完毕,插上清明吊子,供上盆花贡祭,把纸钱柱香点燃,立时腾起片片灰片,升起袅袅青烟。边烧纸钱,边望着父母的墓碑,心里思念父母的恩情,祈祷九泉下的亡灵护佑他们的后代子孙。听人说,现代有人用科技手段证实真有灵魂,我不敢妄断,但我十六年了也无法忘记我父亲临走时的那一幕。那天我冒雨从沙市赶回钟祥,进家只见父亲躺在卧榻上已人事不醒,母亲泪水涟涟,陪我到他跟前,对他说我回来了,父亲只嘴角略略动弹。约摸一小时后,四爸从石牌赶来,坐到他跟前,摸着他的手,说:“昌权也回来了,你就放心去吧!”没过几分钟,父亲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。据四爸留下的自传说,他出生不久我祖父就去世了,而我从来就没见过祖母,由此可知,从年轻时起,他们就双亲俱失,一奶同胞只剩下四爸我爸他们两人。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他们亲密无间,四爸生前,我们家好多事情都请他作主。父亲把他生前的最后一息,留给了他的亲弟弟,这不正是碑刻铭篆的亲亲相连、心心相印吗。我还不能忘记去年发生的一幕。去年春上新冠肆掠,湖北到处封城堵路,清明我不能来钟祥上坟,到了五月十日“母亲节”前夜,居然梦见母亲来向我问长问短,次日我作诗《日前梦母》:细丝夜洒南窗冷,亡母潜来入梦魂。叨问乍风衣少未,开颜门旺喜添孙。醒惊惺眼望故祖,素墓孤碑残旧飧。罹疫清明误节敬,候期北祭报慈恩。母亲节许下的”候期北祭”,到下半年才得以兑现。八月份中元节前夕,疫情渐缓,我便只身来钟祥给父母上坟。时当三伏天午刻,我下车后就直奔坟前。上山的路上没碰到一个人,路边的农家正闭门午休,没见一鸡一犬,只有长一声短一声的“知了”,一路伴我疾行。那天我还去了公墓给岳父母扫墓,从这边山冈到那边公墓要走几里路,来去的路上也没碰到一人一车,顶着烤人的烈日,同窗家彬在家里惦记我,时不时打来电话,生怕我受热中暑。那天,我给父母上坟时整理先前供奉的盆花,没想到花丛里飞出一窝长脚细腰的马蜂,团团围住只穿着T恤短裤的我,蜇得腿上臂上手上脸上到处是包。在片片飞钱袅袅青烟里,四周树上的鸣蝉扯起嗓子嘶叫,正当我望着眼前的碑,胡思乱想莫不是父母责怪我来迟了吧?忽然从右边枝柯丛中传出几声“苦瓜子”鸟的“咕咕”啼叫,仿佛是催促我,结束这次特殊年份的特殊之行。这行程其实是结束不了的,只要是炎黄子孙,对先祖的祭怀,永远在路上。年年清明都会听到杜牧《清明》的吟传,年年清明那些逝去的亲人坟头墓前都会换上新的彩幡,升起袅袅青烟。我这次来给四爸二爸上坟就是这种行程的承续,即使有一天我走不动了,相信还会有后人接力。给二爸上坟费了不少周折。我凭着几年前记忆的方位寻去,坟场中间只有唯一一条小径,一路依然滑着稀泥,稍不留神就有滑倒的危险。这次我在这片坟场穿来穿去几乎找了个把小时,在我寻找的同时,我看到有一男子也举着花提着纸钱,在纸花丛中找来找去,有两次我们还有过交会,我想,他也可能跟我一样被那根无形的线牵着,被磁力吸引着,从异地而来,不谙土地,或是在追索某位旁亲远脉。二爸是二哥昌炎的父亲,我跟二哥同曾祖不同祖父。曾祖传下二子一女,即我祖父、叔祖父和姑婆。二爸是叔祖父的独子,二妈是姑婆的长女,他们是过去讲的“亲上加亲”。二爸其实不满意这宗包办的婚姻,跟二妈生下二哥后就负气离家,其后与胡氏(我们叫胡妈)同居,另立门户生活,二哥则由二妈一人抚养长大成人。记得我小时过年,那时二妈在世,我们给二爸拜年,二哥从不参与。后来二妈病逝,二哥上辈只有二爸嫡亲,时光流淌,慢慢冲淡了父子恩怨隔阂。胡妈没给二爸留下子嗣,晚年两老孤独无依,四爸和二哥时常去照顾,二哥成家后胡妈也曾过来施以援手,帮衬二哥照看过孩子。血浓于水的亲情,渐渐化解了那段由封建传统陋习扭曲编织的亲情隔膜,二爸去世后,二哥将二爸与二妈合葬于一坟,让被封建陋习分离的鸳鸯在另一个世界破镜重圆,比翼于飞。胡妈去世又晚,逝时因二哥远在南隅,胡家后人临时将她葬于二爸坟旁,无碑无字,籍籍无名。二哥退休后长期在东莞照护孙辈,年年清明他都和嫂子回来上坟,这次,他们特意提前回来,在女儿促成下将二爸二妈和胡妈的坟重新修葺,而后将二坟合为一体,修成睡“8”字形状,重修墓碑,将胡妈也列于碑上。我给二爸上坟时,望着碑上一考二妣的碑文,深深感激于二哥和后人的大义至孝,他们以宽博的胸襟释解历史造成的先辈情感上的陈旧纠葛,弥合了不应生出的亲缘嫌隙,致孝于先人,身教于后代,实在可嘉可赞。我把柱香插到两个坟茔上,两个坟茔都插着一枝枝鲜艳的纸花,石牌人纸花作清明吊子,一束纸花就是一个招魂的彩幡,我想,那九泉之下,二爸二妈胡妈他们一定是聚在一起,听着几辈的后人从几千里外结成队特来对他们的问候,接受子孙们的探望吧。连绵几天的雨驻脚了,西方天空上断续现出一缕缕阳光,化开一脸阴郁,散开的云衢之间镶嵌一方方彤云,仿佛晚霞浸染的锦罗。在淡阳斜照下,四周的青葱围着这方红绿粉白的清明的斑斓,微风轻漾,纸花轻轻曳动,仿佛彩幡摇荡。又有几处响起爆竹,那是上坟的最后仪式,响处腾起股股浓烟,又很快化为淡淡青烟,青烟带着亲人的长思,袅袅消失于广漠的苍穹。#文化快讯#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kushiliana.com/kslry/1173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时光清浅,岁月安然,我与多肉共赴美好
- 下一篇文章: 新手养多肉,选对品种,轻松养出肉墩子